首頁 > 行業動態
中國企業海外尋礦的難題
作者:管理員 時間:2012-06-26

中信泰富(Citic Pacific)主席常振明對其公司的中澳鐵礦項目(Sino Iron)的重要性毫不含糊。他說:“全中國都在盯著這個項目。”該礦位于西澳大利亞覆蓋著紅色土壤、荒涼的皮爾巴拉(Pilbara)地區。
更確切地說,中國正在膽戰心驚地盯著這個項目,因為這家在香港上市的企業正在面臨日益超支的成本和反復拖延。由此導致的代價非常高昂。常振明表示,中澳鐵礦項目的規模是國內最大的鐵礦石項目的四倍。
盡管外界觀察人士常常擔心,中國企業是一股無法阻止的巨大力量,大量攫取全球礦產資源,但這種看法并不準確。中國在全球的資源擴張并非一帆風順。
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直希望,通過持有巨額礦產份額,并從必和必拓(BHP Billiton)、淡水河谷(Vale)和力拓(Rio Tinto)手中奪取大宗商品定價權,它將能夠更容易掌控自己的經濟命運。
但中澳鐵礦項目不僅沒能展示中國的力量,反而成了一個警示性故事,凸顯出中國企業在尋求海外擴張時遇到的困難。當2006年最初構想該項目時,總成本估計不到20億美元。但現在,中信泰富已經耗費了71億美元。花旗集團(Citigroup)的分析師估計,該項目的成本有可能暴漲至93億美元,還有人稱,預計最終成本將更接近100億美元。該礦的進度至少已經拖延了兩年。
一家在澳大利亞擁有廣泛外包業務的亞洲領先交易企業的一名高管表示:“現在問題已經不再是關于商業目標了,而是關乎中國人的面子。他們砸了太多錢進去,已經難以抽身。”
其實,它不僅僅關乎面子。中國需要進口60%左右的鐵礦石,該項目是中國試圖擺脫外國供應商挾制的重要嘗試。中國鋼鐵企業一直指責外國供應商把鐵礦石價格抬得過高。
匯豐(HSBC)的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這樣描述該行業的趨勢:“中國一直被少數幾家企業牽制著。現在中國不想繼續被動地做鐵礦石的買家。中國想開發新的原材料來源,想要持有項目的股份。”
但中澳鐵礦項目的問題表明,中國想做到這一點依然步履維艱。中國企業想要證明,它們擁有在不同于祖國的環境中工作所需的專門技術和管理技能,但力不從心。
在國內,中國企業長期以來在政府的羽翼保護下安逸地經營,面對國外激烈競爭時往往措手不及。而勞工法律和合同性質方面的文化差異尤其令它們苦惱。
中澳鐵礦項目不是中國唯一一個在西澳大利亞出現困難的項目。該地區有14個重要鐵礦石項目。其中8個有來自中國的投資,銀行家表示,有些項目同樣受到拖延和成本超支的困擾。
中國鞍鋼集團(Anshan Iron & Steel)和澳大利亞金達必金屬公司(Gindalbie Metals)斥資26億美元成立的卡拉拉(Karara)鐵礦石合資企業,被基礎設施設計變更、材料和勞動力成本飆升以及匯率變動等問題壓得不堪重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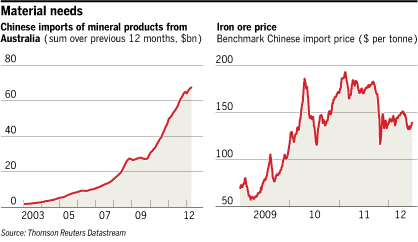
有些情況純屬運氣不佳。但多數情況下,出現問題部分是由于對項目各個環節估計過于樂觀:從當地工人的生產率到東道國政府對環境的關注,而這些問題在中國國內都不是問題。
中國難以現實地預測海外項目成本,這個問題不僅僅局限于采礦業。
中國內地一家企業在香港上市的子公司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China Railway Construction Corp)去年表示,由于建造成本超過預算,該公司承建的從麥加(Mecca)到沙特阿拉伯其他幾座城市的輕軌鐵路線路預計虧損40億元人民幣(合6.28億美元)。
令人尷尬的是,該項目曾引起高度關注。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沙特國王都出席了簽約儀式。最終,該項目轉交給了中國鐵建的國有母公司,以控制這家上市公司的虧損和未來義務。現在,預計中國政府將為沙特政府意外調整項目、變更要求,向該公司提供補償。
當然,中國也曾成功地管理某些外國企業,例如2010年吉利(Geely)收購的沃爾沃(Volvo)。中國石油企業的身影也出現在遙遠的非洲和拉丁美洲。
但中國政府的戰略制定者尤其關注礦產項目,而一系列常見的困難反復阻礙該行業中國企業在海外的努力。
引發嚴重誤解的問題尤以礦山勞工為甚。
中國的采礦計劃要求使用成本低、生產率高的中國工人。但澳大利亞勞工法和簽證要求卻構成障礙。相反,這些項目依賴澳大利亞昂貴的工人。在澳大利亞,即便是卡車司機年薪都達20萬美元,住著三室的房子,每兩周享有一次帶薪探親假——某些時候這意味著飛往巴厘島。盡管中國人認為支付的薪酬已經相當可觀了,但依然面臨勞資沖突。
進一步說,中國企業希望能夠左右它們在項目中的命運,這也是它們沖向海外的初衷。這和日本人不同,日本人學會了——至少在最初階段——選擇持有少數股份,更多地依靠當地合作者。中國尋求控制權,因此談判會出現沖突,尤其是中國人通常不愿意向當地的咨詢公司支付高額費用。
另外,律師們表示,中國人傾向于在合同中使用模糊語言。在中國,這種做法是說得通的,因為那里的情況會迅速發生變化,雙方都明白,合同只是談判的一個起點,而非板上釘釘、不可改變。
中國企業存在一個人們不那么熟知的缺陷:它們有時會發生內訌,幾乎不會一味執行中國政府下達的中央任務。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中國企業正演變為有著利益沖突的商業化企業。一家領先國際銀行項目融資部門的一位銀行家表示:“中國及其銀行正在脫離中國公司(China Inc)的模式。”
更特別的是,中澳鐵礦項目的所有主要參與者——持有該項目80%股權的中信泰富、該項目主要貸款銀行中國國家開發銀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持有該項目剩下20%股權的主要承包商中國中冶(China Metallurgical)——正在發生口角。知情人士稱,國開行希望退出該項目,而中信泰富一直考慮以拖延工程進度以及預算超支為由起訴中冶。據直接了解此事的一位人士表示,最近這一爭議已提交國務院處理,負責金融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對此做出了裁決。中信泰富拒絕置評。
對于國開行為該項目提供融資的人士而言,該項目尤其令人失望,該銀行已貸出近50億美元。中澳鐵礦項目正是國開行有意提供資金的那類項目,該銀行是一家未上市的政策性銀行,其優先任務由中國政府確定。6年前,當該項目首次被提出時,中國急需鐵礦石,用以煉成鋼鐵,而鋼鐵是眾多商品的重要原材料,從汽車到資本設備,從住宅樓到鐵軌。
然而,市場已發生變化。中國的礦產企業正開始意識到,它們是在鋼鐵周期的一個錯誤時刻計劃大量生產鐵礦石的,這一發現令人膽戰心驚。在該項目首次被提出后的5年里,中國的鋼鐵需求增速一直下滑,價格也一直下跌。2010年,中國的鐵礦石進口出現同比下滑,這是10多年來的首次。2011年,緊縮的貨幣政策和對房地產建設的嚴格限制,繼續令鋼鐵價格面臨下行壓力。
如果這還不夠讓人頭疼的話,對于匯率的錯估助推了成本上漲。在該項目整個周期中,澳元升值,中信泰富買入的頗具爭議的對沖產品押錯了方向,導致20億美元虧損以及高管離職。
澳大利亞政府計劃從7月1日開始征收礦產資源租賃稅(Mineral Resources Rent Tax),這將進一步削弱礦業項目的盈利能力,就像對碳排放征稅一樣。
盡管母公司中信集團(Citic Group)令人敬畏,但中澳鐵礦項目面臨的難題仍使中信泰富被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列為垃圾級。從官方上來說,中信泰富直接受中國國務院的管理。券商里昂證券(CLSA)表示,由于中澳鐵礦項目,這家還擁有公用事業機構的綜合企業的市值應較其資產凈值有45%的折讓。
過去,中國政府一直不讓國企為失敗承擔責任。如今,隨著失敗項目導致的虧損增加,國內外的情況都發生了變化。
實際上,國資委最近曾呼吁下屬企業改善它們對海外業務的管理。在一次不同尋常的公開譴責中,中國媒體引用國資委的話斥責國企浪費金錢。
例如,去年6月,中鋼(Sinosteel)叫停了另一個鐵礦石項目Australian Weld Range,2008年,中鋼以13.6億澳元收購該項目。該項目依賴Oakajee港口和鐵路項目來運輸鐵礦石,但這個項目也出現了問題。擬議的解決方案之一是中鋼購入Oakajee項目的一半股權。但中國政府免去了中鋼總裁黃天文的職務,同時業內消息人士表示,中國政府不太可能批準此類交易。
與此相符的是,一些跡象表明,中國現在正在減少大舉花錢的計劃。國開行正明顯變得更為謹慎。國有的中國中鐵(China Railway Engineering Co)組建了一家合資公司,以在印尼修建一條煤炭運輸鐵路。在過去,這原本似乎是一個非常明顯的國開行項目,但現在國開行希望,包括外國合作伙伴在內的出資方可以為貸款擔保,以避免中澳鐵礦項目失敗的例子重演。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這是一個不錯的項目,但進展緩慢,這意味著,韓國人可能會攪局。”
隨著中國人對于擴張變得更為謹慎,希望填補他們留下的空缺的將不僅僅是韓國人。
英國《金融時報》何麗(Leslie Hook)補充報道







